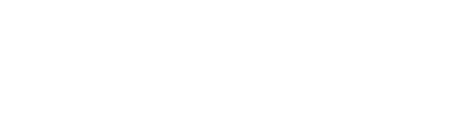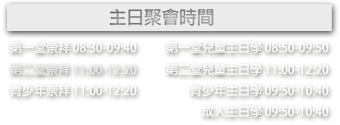隔離的教會,不變的使命
台灣突然爆發的疫情觸動了我一年前的回憶—當時我們一家已經準備要回台投入竹北勝利堂的青少年事工,美國疫情大爆發,突然間頒布封城令,航班紛紛被取消,台灣這邊也限制外籍人士(包括Heather和當時還沒取得國籍的Jessie)入境。另一方面,美國的教會全面改為線上進行,各地的華人教會想破頭開發各種可以在線上玩的破冰遊戲、在不直接接觸的情況下進行的社群互動方式(例如所有人約好一個時間開車到壽星的家門口按喇叭慶生)、並嘗試解決無法實體領聖餐的問題。
牧養的工作畢竟是「鐵磨鐵、實打實」的關係建立和生命陪伴,當線上聚會成為常態,起初的一些優勢:例如比以往更容易請到大牌講員、例如各樣的線上訓練和課程大行其道、例如待在家的弟兄姐妹有比以往更多的時間參與聚會……。這一年下來美國華人教會大多經歷了一定程度的疲乏和萎縮:線上的新鮮感很快就會過去,缺乏實際生活經驗連結的一群人越來越缺少動力「刻意」地去維繫和彼此的關係……。
線上聚會對教會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挑戰,我自己作為青少年學生的工作者,更有一種雙手雙腳被綁住的感受。
這種無能為力的感受卻也讓我想起獄中的保羅。當時他只能藉由書信牧養教會,而他留下的文字情深意切,充滿著對羊群的掛念:「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地祈求。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腓1:3-5)
我也想起二戰時期因為計劃行刺希特勒而在獄中被處死的德國信義宗牧師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他在「團契生活」(Life Together)這本小書中說到「信徒之得以和其他信徒一起過活,並不是甚麼理所當然的事。試想想,耶穌基督生活在仇敵中間,最後,祂所有的門徒都離開了祂。在十字架上,衪完全被孤立,周遭全是作惡者和嘲弄衪的人。然而,祂來到世上,正是為了這些緣故,要將平安帶給敵擋上帝的人。既然如此,信徒…乃要活在仇敵當中。」
無論是保羅、是潘霍華、還是我們的主基督耶穌,他們都在「隔離」中建造教會,也在「隔離」中完成他們的使命。我相信因為「隔離」,他們的心更為迫切,也更為火熱。
從人的角度,隔離不是最理想的牧養方式,但是當隔離成為常態,當我們不再能按著習慣的方式「正常生活」,疫情幫助我們儆醒,認識到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是被罪和死所污染、充滿著破碎和傷痕。也因此我們更加渴慕神國的救恩,也求神使用隔離中的我們,在疫情中成就祂的工作,和祂對這世界不變的使命。